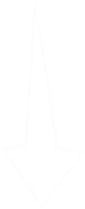那一把棉花温暖我到如今。

上午在开着暖气的房间里,我竟感到一丝寒意,就在单衣外面加了件背心,霎时感觉暖和了许多。在这冷暖转换的瞬间,我想起万里之外的母亲,想起她在几十年前的严冬如何帮我御寒。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候的冷,是天寒地冻,是无缝不入,是几尺长的冰凌儿挂在屋檐下几个星期都不掉下来,是池塘里的水冻成了深绿色的玻璃,鱼在里面封住动弹不得。
几乎每个冬天,我的手上、脚上都会留下冻疮。上小学的我感觉冬季每天的晨读课是那么难熬。学校没钱给教室的所有窗户安装玻璃,就用尼龙纸糊住窗扇;风会把窗纸刮得啪啪地响,那响声与孩子们冻得直抽鼻涕的声音此起彼伏;教室单薄的土墙既不保暖也不隔冷,室内室外温度几乎一样。每个人的手和脚都冻得生痛,一心盼着下课铃早点响起,可以回家吃早饭。
童年时有许多游戏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开心,只有一样除外:一个年级的孩子涌到墙角,大家挤在一起,摩擦生热,我们称之为“挤暖”。这个游戏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都玩。我们的身体和衣服把墙角磨得光滑,但暖和只保持在挤挤攘攘的那一会儿——大家四散之后回到教室,冷更甚于“挤暖”之前。
母亲是位裁缝,手艺很好,东家请西家接地到人家家里做衣裳,按说应该有些收入,但大多数农户都穷,做衣服的费用往往要拖到“年关”才结算,甚至要赊好几年。母亲东拆西借,缝缝补补,尽量让四个儿子穿暖些。每个冬季,我都穿上了棉袄,但我的棉袄袖子总是短了一截儿——其实并不短。我性别意识觉醒得早,母亲给我做的冬衣的里子,用了些红绿的布料我将就了,但冬衣的面子有时竟有一小半是深红色的,甚至还带点图案。我已顾不得那么多,因为实在太冷,也没有选择了。
我后来明白有衣服穿就已经很不错了。那时正赶上经济困难时期,买布料要凭“布票”。爸爸是家里的劳力,我们放寒假时他也得早出晚归干农活,有时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参加“兴修水利”的工程。家里最困难时,粮食不够吃,奶奶要保证家里主要劳力一天三餐伙食,不得不狠心只给我们吃两顿主食——晚上让我们吃点炒米之类的东西,就很早哄我们钻进被窝,因为被窝里暖和,睡着了晚餐也省了。
这么冷的天,母亲也得天天赶路,去给人家做衣裳。她系着一条鹅黄色的有凤凰图案的围巾;围巾很好看,但其实很单薄,围着它抵御朔风,聊胜于无。她脸上、手上也有好几处冻疮。
我猜想我的母亲在给富户人家的孩子缝制厚棉衣时,一定想起了她的儿子,特别是她的那位叫冷叫得最厉害的二儿子,也就是我。这个猜想的证据是:有一天母亲收工回家,给我带回了一把棉花。她把棉花扯开了塞进我的暖鞋和针织手套里,让我这样穿戴着上学。
我记不起来那是不是真的就让我暖和些了;我只记得母亲很认真地塞棉花,我在一旁也很认真地看着,毫不怀疑那样会让我更暖和些。我还记得也就是在那前后,爸爸妈妈为给我治冻疮,在灶火里把萝卜烧得半熟,用热萝卜擦拭我脚部和手背冻伤的地方。
那一把棉花,我记到了今天。
依稀听母亲讲,她三四岁时,那还是在1949年前,随着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到外村要饭。她那时候是懵懂的小女孩;她妈妈会把乞讨到的热饭菜留给她。这是在那样的处境中她的母亲唯一能做到的。
母亲在严寒的冬天,在冬衣御寒不够的情况下,那么无奈而又自信地给我鞋子里、手套里塞上一把棉花。这是在那样的处境中我的母亲唯一能做到的。
那一把棉花啊,温暖我到如今。(赵焕新)
本文链接:http://www.gihot.com/news-1-11048-0.html晨读 | 赵焕新:一把棉花
声明:本网页内容旨在传播知识,不代表本站观点,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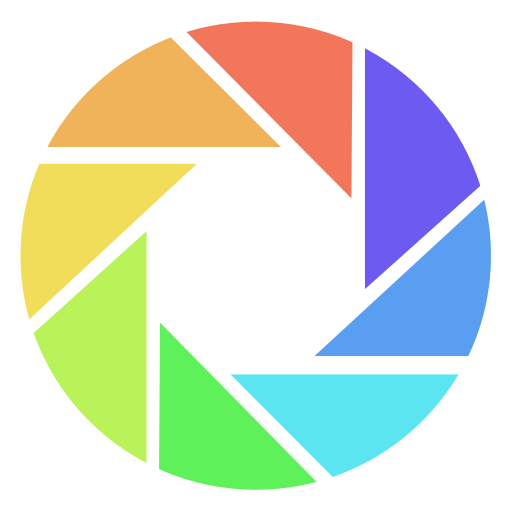 朋友圈
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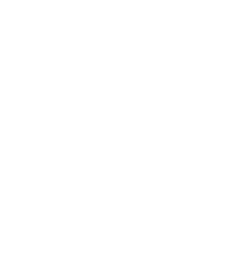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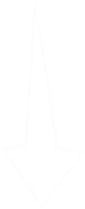
点击右上角 QQ
Q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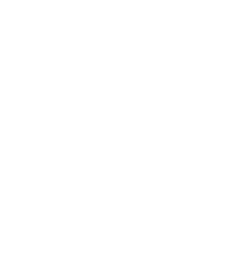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QQ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QQ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