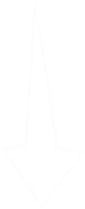6月的新奥勒松,哪怕是午夜,阳光依旧刺眼。这个位于挪威斯瓦尔巴群岛上的小镇,地处北纬79度,是人类在地球上的最北定居点之一,也是科学界闻名的极地“科考圣地”。
2004年7月,一对中国石狮“落户”新奥勒松,标志着中国首个北极科考站——黄河站正式建站。20年来,黄河站始终是中国北极科考的“大本营”,共有660多位中国科学家来到这里,进行冰川、陆地、海洋、大气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和实验,为研究极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着“中国力量”。
中国北极科考“大本营”
中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1925年,中国加入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有权自由进出北极特定区域,并依法在该特定区域内平等享有开展科研以及从事生产和商业活动的权利。1999年,“雪龙”号极地考察船首次赴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任务。2004年7月,在各方积极努力下,中国在北极地区的首个科学考察站——黄河站在新奥勒松建成。
“黄河站是我们北极科考的‘大本营’。自2004年建站以来,黄河站支持了包括冰川学、陆地生态学、海洋生态学、空间物理学、大气和地理信息等各个专业领域的科学观测、监测和研究。黄河站为我国极地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为我国科学家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河站站长胡正毅告诉记者。
据胡正毅介绍,截至2023年底,黄河站累计支持250多个业务和科研项目,保障660多位科考人员赴站进行科学考察。通过黄河站和“雪龙”号、“雪龙2”号等船站平台,中国在北极地区逐步建立起冰川、海洋、大气、生物、地质等多学科观测体系,涵盖科学研究、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
极地科考合作的重要平台
挪威极地研究所特别顾问金·霍尔门教授至今仍能回忆起2004年黄河站成立时的场景。他是黄河站的“老朋友”,甚至参与了建站前的预备会议。黄河站建站20年来,他与不少来黄河站科考的中国科学家成为挚友,进行广泛交流合作,共同研究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来黄河站从事科考工作的中国科学家非常勤奋,都受过良好教育,待人温和谦虚,他们为极地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霍尔门说,他和挪威极地研究所的同事都很乐意与中国科学家进行学术探讨。“气候变化在北极发生得最快、最剧烈。我相信,通过与中国科学家的共同研究,我们可以预测世界其他地区可能出现的气候变化,这对科学研究和人类命运至关重要。”
正在黄河站驻站的同济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赵红颖教授告诉记者,她正在进行同济大学领衔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我这次来北极的实验任务是对北极地区海洋及大气中的微塑料进行检测和溯源。”她介绍说,中国环境、海洋、化学等学科的许多科研人员都参与了极地相关的研究课题,黄河站搭建的极地实验平台对相关研究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黄河站的平台,我可能就无法顺利地完成在极地的实验。”
“我们经常去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也很欢迎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来新奥勒松,我们合作得很好,黄河站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参与上述国际合作项目的挪威极地研究所生态毒理学负责人盖尔·加布里埃尔森教授表示,他们期待与更多来黄河站科考的中国科学家交流。
不期而至的危险和“日以继日”的工作
极地科考与危险和艰苦相伴。在黄河站外仅二三十米的地方,就竖着一块“北极熊危险”的警告牌,要求人们必须配枪才能离开新奥勒松镇区。
科考队员、同济大学博士生武小涵告诉记者,6月15日,在她抵达黄河站不久,就看到了新奥勒松管理方发布的北极熊警告:有一头北极熊在距离黄河站不到1公里的小岛上活动,随时可能对科考队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6月25日,另一头北极熊又出现在相近位置。“我从未想过危险会离自己这么近。”
除了不时出没的北极熊,冰川上的裂隙、海洋中的冰山、突然降临的暴风雪等都会对科考队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科学考察的工作强度也是一大考验。记者与胡正毅一起去冰川取样,往返花了7个多小时,也只走到距离最近的一个观测取样站点。胡正毅告诉记者,如果去最远的冰川取样点,可能要花10多个小时走上20多公里。夏季的北极并无昼夜之分,24小时都是极昼。有时候上午出发,虽然回来时太阳仍然高悬,但已是凌晨两三点。
“虽然苦,虽然累,虽然有危险,但结束工作回到站里,看到门口黄河站的牌子,看到会议室里鲜艳的五星红旗,便感到自己为中国极地科考付出的汗水是值得的。”胡正毅告诉记者,黄河站建站的20年,也是中国极地科考事业不断发展、不断突破的20年。近年来国家对黄河站的投入不断增加,各项实验仪器和设备逐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坚信黄河站的未来一定会更好,中国极地科考的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
6月的新奥勒松,哪怕是午夜,阳光依旧刺眼。这个位于挪威斯瓦尔巴群岛上的小镇,地处北纬79度,是人类在地球上的最北定居点之一,也是科学界闻名的极地“科考圣地”。
2004年7月,一对中国石狮“落户”新奥勒松,标志着中国首个北极科考站——黄河站正式建站。20年来,黄河站始终是中国北极科考的“大本营”,共有660多位中国科学家来到这里,进行冰川、陆地、海洋、大气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和实验,为研究极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着“中国力量”。
中国北极科考“大本营”
中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1925年,中国加入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有权自由进出北极特定区域,并依法在该特定区域内平等享有开展科研以及从事生产和商业活动的权利。1999年,“雪龙”号极地考察船首次赴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任务。2004年7月,在各方积极努力下,中国在北极地区的首个科学考察站——黄河站在新奥勒松建成。
“黄河站是我们北极科考的‘大本营’。自2004年建站以来,黄河站支持了包括冰川学、陆地生态学、海洋生态学、空间物理学、大气和地理信息等各个专业领域的科学观测、监测和研究。黄河站为我国极地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为我国科学家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河站站长胡正毅告诉记者。
据胡正毅介绍,截至2023年底,黄河站累计支持250多个业务和科研项目,保障660多位科考人员赴站进行科学考察。通过黄河站和“雪龙”号、“雪龙2”号等船站平台,中国在北极地区逐步建立起冰川、海洋、大气、生物、地质等多学科观测体系,涵盖科学研究、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
极地科考合作的重要平台
挪威极地研究所特别顾问金·霍尔门教授至今仍能回忆起2004年黄河站成立时的场景。他是黄河站的“老朋友”,甚至参与了建站前的预备会议。黄河站建站20年来,他与不少来黄河站科考的中国科学家成为挚友,进行广泛交流合作,共同研究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来黄河站从事科考工作的中国科学家非常勤奋,都受过良好教育,待人温和谦虚,他们为极地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霍尔门说,他和挪威极地研究所的同事都很乐意与中国科学家进行学术探讨。“气候变化在北极发生得最快、最剧烈。我相信,通过与中国科学家的共同研究,我们可以预测世界其他地区可能出现的气候变化,这对科学研究和人类命运至关重要。”
正在黄河站驻站的同济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赵红颖教授告诉记者,她正在进行同济大学领衔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我这次来北极的实验任务是对北极地区海洋及大气中的微塑料进行检测和溯源。”她介绍说,中国环境、海洋、化学等学科的许多科研人员都参与了极地相关的研究课题,黄河站搭建的极地实验平台对相关研究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黄河站的平台,我可能就无法顺利地完成在极地的实验。”
“我们经常去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也很欢迎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来新奥勒松,我们合作得很好,黄河站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参与上述国际合作项目的挪威极地研究所生态毒理学负责人盖尔·加布里埃尔森教授表示,他们期待与更多来黄河站科考的中国科学家交流。
不期而至的危险和“日以继日”的工作
极地科考与危险和艰苦相伴。在黄河站外仅二三十米的地方,就竖着一块“北极熊危险”的警告牌,要求人们必须配枪才能离开新奥勒松镇区。
科考队员、同济大学博士生武小涵告诉记者,6月15日,在她抵达黄河站不久,就看到了新奥勒松管理方发布的北极熊警告:有一头北极熊在距离黄河站不到1公里的小岛上活动,随时可能对科考队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6月25日,另一头北极熊又出现在相近位置。“我从未想过危险会离自己这么近。”
除了不时出没的北极熊,冰川上的裂隙、海洋中的冰山、突然降临的暴风雪等都会对科考队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科学考察的工作强度也是一大考验。记者与胡正毅一起去冰川取样,往返花了7个多小时,也只走到距离最近的一个观测取样站点。胡正毅告诉记者,如果去最远的冰川取样点,可能要花10多个小时走上20多公里。夏季的北极并无昼夜之分,24小时都是极昼。有时候上午出发,虽然回来时太阳仍然高悬,但已是凌晨两三点。
“虽然苦,虽然累,虽然有危险,但结束工作回到站里,看到门口黄河站的牌子,看到会议室里鲜艳的五星红旗,便感到自己为中国极地科考付出的汗水是值得的。”胡正毅告诉记者,黄河站建站的20年,也是中国极地科考事业不断发展、不断突破的20年。近年来国家对黄河站的投入不断增加,各项实验仪器和设备逐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坚信黄河站的未来一定会更好,中国极地科考的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
本文链接:http://www.gihot.com/news-2-7716-0.html北纬79度的中国北极科考“大本营”
声明:本网页内容由互联网博主自发贡献,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天上不会到馅饼,请大家谨防诈骗!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
上一篇:全球首列商用碳纤维地铁列车问世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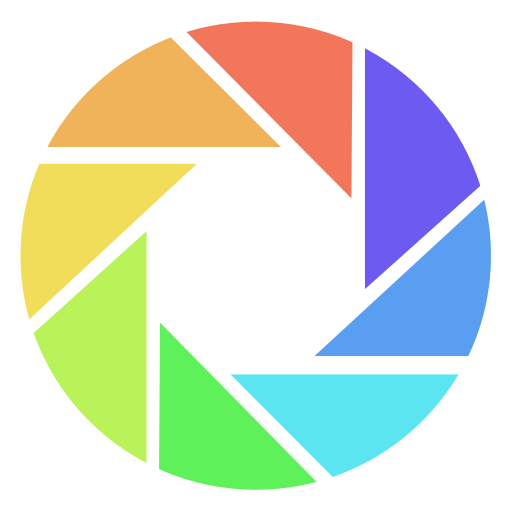 朋友圈
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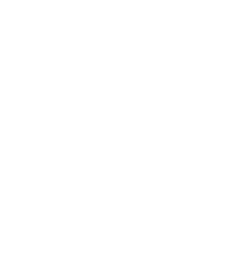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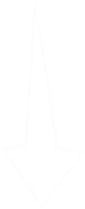
点击右上角 QQ
Q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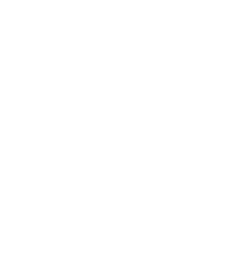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QQ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QQ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