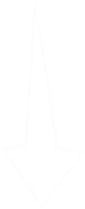生活有个“契诃夫结”:读契诃夫
culture.ifeng.com 2024年07月17日 10:23还是米沃什一语中的: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都在消化从欧洲传进来的科学和形而上学。这些陌生的新知识,成了对俄罗斯生活和信仰的解构力量。欧洲的土壤生产了它们,也自有办法消化它们。俄罗斯没有。这就是19世纪特有的、俄罗斯式的焦虑[1]。
遵循米沃什的指引,我才意识到俄罗斯小说的“神学味”。这味道,不只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也出现在托尔斯泰身上,甚至还出现在笃信科学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医生身上。19世纪的俄罗斯小说,很像18世纪的康德形而上学。后者要在心灵中给上帝留个位置,前者要在生活中给上帝留个位置。即便不大热衷谈论上帝的契诃夫,也有这个冲动。
这是一篇想了很久的笔记。拟题目时就犯了犹豫:《生活有个“契诃夫结”》不错,《读托尔斯泰的契诃夫》也不错。“契诃夫结”,是最近一年重读契诃夫时不知怎么冒出来的怪词。合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让人惆怅的剧本和小说,心里空落落的,就剩下这个词。托尔斯泰,是我读契诃夫的参照,可能也是契诃夫为自己设立的参照。契诃夫看重托尔斯泰,我很晚才知道。但我很久以前就隐隐觉得,他俩很像。那种像,不是文体上的、风格上的、观念上的像,而是某种“基本问题”上的像。酷暑和严寒里的两个人,哪里都不像;盼着好天气,却是他们共同的“基本问题”。从同一个“基本问题”出发,托尔斯泰写出了生活的沦陷之痛,以及英雄式的悔改。到了契诃夫那里,痛与悔变成了一种晦暗的忧郁,不强烈,却黏稠难散,弥漫人心。无以名之,我叫它“契诃夫结”。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
伯林有个著名的譬喻:狐狸多智,刺猬终生求一大智。据伯林观察,托尔斯泰明明是天生的狐狸,却误以为自己是刺猬,于是从艺术进入宗教,求信而不得,终生痛苦。要是套用伯林的譬喻,契诃夫肯定属于杰出的狐狸,并且安于当狐狸:一支笔写尽俄罗斯心灵万象,准确,节制,点到即止。契诃夫喜爱、敬佩托尔斯泰,首先也是因为他那巨大的狐狸式才华。契诃夫的书信里经常提到《克莱采奏鸣曲》《战争与和平》《复活》《霍尔斯托梅尔》。他惊赞的,是托翁那支随物赋形运转自如的如椽巨笔。可是,一触及托翁钟爱的主题,契诃夫总是忍不住发发牢骚。
托翁的主题,当然是城市精英的堕落,是科学、现代哲学、进化论对心灵的蒙蔽,是乡村农耕生活的救赎力量,是人为何不信、如何得信的“基本问题”。对这些,契诃夫不耐烦。契诃夫是农民的儿子,也是医生。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深知农村生活的实情。他眼里的农民、农村,不是托翁式的渴求悔过自新的庄园主眼里的农民、农村。作为医生,契诃夫相信科学可以改善生活,相信同胞必定因为生活的改善变得更体面、更良善。因此,托翁那种对科学的敌视、对医学的无知,契诃夫颇为反感。总之,每当托翁要从狐狸转向刺猬的时候,契诃夫就感到不适。
事情似乎很简单:狐狸契诃夫,喜欢托尔斯泰的狐狸的一面。事情又似乎不那么简单:契诃夫从来也不曾摆脱那个刺猬托尔斯泰;困扰着刺猬托尔斯泰的问题,也以另外的方式困扰着他;特别是当他发现,不能用托尔斯泰的方式解答托尔斯泰的问题时,困扰加倍了。下面是两封信:
托尔斯泰的教义不再感动我了,现在我内心深处对它没有好感,而这当然是不公道的,在我身上流着农民的血,因此凭农民的一些美德是不能使我感到惊讶的。我从小就信仰进步,而且也不能不信仰,因为在打我和不再打我这两个时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托尔斯泰的哲学曾经强烈地感动过我,它控制了我六七年,而且对我起作用的并非一些基本论点,因为这些论点我以前也知道,而是托尔斯泰的表达方式,他的审慎明智,可能还有他那种独特的魅力。现在呢,我心中有一种东西在抗议……不管怎样,托尔斯泰已经消失,我心灵中已经没有他了,而他在从我心中出走时说:我把您的空房子留下来。现在没有什么人留宿在我的心灵中了。[2]
我怕托尔斯泰去世。如果他死了的话,那在我的生活中就会形成一块大空白。第一,我没像爱他那样地爱过任何一个人;我不是教徒,但在一切信仰中我认为正是他的信仰对我来说最亲切和适宜。第二,如果托尔斯泰还在文学界,那么做一个文学家是件轻松而又愉快的事情;甚至在想到自己什么也没有做或不在做的时候也不感到可怕,因为托尔斯泰代大家做了。他的活动是对文学的种种期望和信赖的保证。第三,托尔斯泰脚跟站得稳,他的威望巨大,因此只要他还在,文学中的不良趣味、庸俗作风(厚颜无耻的和哭哭啼啼的庸俗作风)、各式各样粗糙的充满怨气的自尊心就都不会抛头露面。单凭他的道德威望就能使所谓文学界的士气和流派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没有了他的话,就会是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或者就会是乱糟糟的一团。(1900年1月28日)[3]
这里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在同各种辱没信仰的现代哲学辩论之后得出了一种替代哲学的托尔斯泰。在各种主义泛滥的19世纪末,他又为世人提供了一种托尔斯泰主义。另一个是诚实刚毅坚韧如圣徒的托尔斯泰,那是活生生的人,充实而有光辉的人。托尔斯泰主义,本是托尔斯泰这个人困而思之的文字记录。它曾经影响了很多人,包括契诃夫。但契诃夫渐渐觉得不满。对他而言,托尔斯泰主义对制度、时代、人性的意见太武断,有时还很无知;托尔斯泰主义对上帝和永生的论述,契诃夫也觉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托尔斯泰主义,曾经为契诃夫提供了一套对世界的看法、说法。那套看法、说法不再重要。因此,“托尔斯泰已经消失,我心灵中已经没有他了”。可是,托尔斯泰这个人,仍然重要,始终重要。不再需要托尔斯泰主义的契诃夫,仍然害怕失去托尔斯泰。因为托尔斯泰代表着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为了一个困惑、一个理想,刚猛沉毅,穷探力索。是托尔斯泰提出了托尔斯泰主义,不是托尔斯泰主义造就了托尔斯泰。事实是,托尔斯泰主义造就不出托尔斯泰。这就是契诃夫面临的困局:他的时代,不乏托尔斯泰主义者,却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托尔斯泰。人们不满意托尔斯泰给出的答案,同时也丧失了托尔斯泰那样的严肃面对问题的能力和勇气。舍弃托尔斯泰主义,契诃夫并不觉得空虚。因为他更满足于观察、探究具体的生活,不太急于为世界下结论。可是,想到可能失去托尔斯泰这个人,契诃夫会觉得不安。因为那代表着整个时代的空虚。空虚,不在于缺少答案,而在于人们渐渐不愿面对问题。
托尔斯泰的小说,总要有一个独自面对问题强探力索的自传人物:《战争与和平》的皮埃尔,《安娜·卡列尼娜》的列文,《复活》的聂赫留朵夫,甚至《伊凡·伊利奇之死》的伊凡。契诃夫描写的,则是隐隐觉得缺了点儿什么的整个时代。托尔斯泰让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承担问题。契诃夫让整个时代承受空虚。他承认,自己也在这空虚之中。
托尔斯泰有狐狸的才能,契诃夫也有。托尔斯泰有刺猬的痛苦,契诃夫也有。托尔斯泰式的刺猬说:问题很明确,必须找到答案。契诃夫式的刺猬说:答案不对劲儿,问题也渐渐不明朗,因此必须忍受入骨蚀肌的空虚。
二十九岁的契诃夫写了一篇《没意思的故事——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人们觉得,它很像托尔斯泰那篇《伊凡·伊利奇之死》。两者都写功成名就的老人的死、死前的懊悔、懊悔引发的对生活的重审。但是,它们的情调很不一样。托尔斯泰留给伊凡的道路是明确的:死只是一道门槛,重要的是死之前的悔改,和死之后的那扇门。托尔斯泰为读者提供了极尽平庸的反传奇生活和惊心动魄的死亡体验,两种写法加在一起,却串联出一个关于悔改和重生的神学故事。契诃夫则不是。他关注的,就是生活里那无法表达的空虚。谁被它抓住,谁的生活就完了。他的男主角说:
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我想了又想,想了很久,什么也想不出来。不管我怎样费力地想,也不管我把思路引到什么地方去,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里缺乏一种主要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东西。我对科学的喜爱、我要生活下去的欲望、我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的静坐、我想了解自己的心意,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来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凡是我对科学、戏剧、文学、学生所抱的见解,凡是我的想象所画出来的小小画面,就连顶精细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作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可是如果缺乏这个,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在这样的贫乏下,只要害一场大病,只要有了对死亡的畏惧,只要受到环境和人们的影响,就足以把我从前认为是世界观的东西,我从中发现我的生活意义和生活乐趣的东西,一齐推翻,打得粉碎。因此也难怪那些只有奴隶和野人才配有的思想和感情把我一生中最后这几个月弄得十分暗淡,到了现在,冷冷淡淡,连黎明的曙光也无心去看了。如果一个人缺乏一种比外界的一切影响更高超更坚强的东西,那么当然,只要害一回重伤风就足以使他失去常态,一看见鸟就认为是猫头鹰,一听见声音就以为是狗叫。在这种时候,所有他的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以及他的伟大和渺小的思想,就只有病症的意义,没有别的意义了。[4]
本文链接:http://www.gihot.com/news-2-9309-0.html为大家揭晓拼多多额度怎么套出来有几个步骤(仅供参考)
声明:本网页内容由互联网博主自发贡献,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天上不会到馅饼,请大家谨防诈骗!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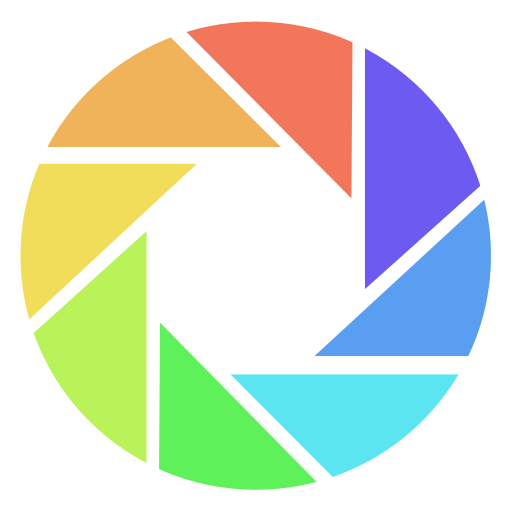 朋友圈
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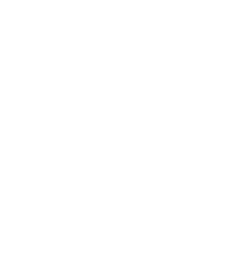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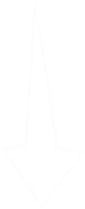
点击右上角 QQ
Q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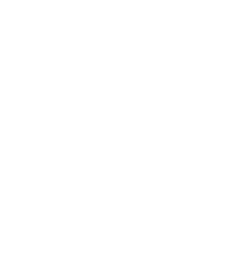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QQ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QQ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