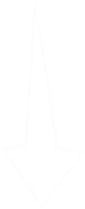大众网记者 王一刚 报道
日月开新元,万象启新篇。2月10日,济南市历下区历山双语学校召开2025年高品质发展大会。
会议由行政后勤副校长周林主持。
山东师大基础教育集团执行总经理、学校党支部书记陈仁波在讲话中指出,面对当今社会的新发展态势,双语全体教职员工要明晰方向、明确路径、理清思路、精准思考、细化目标,以小目标的不断完成,实现大目标的有效达成。以坚定的信念,果敢的行动,高效的执行力,在集团全力构建资源平台的契机下,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为集团的发展贡献自身价值。他要求,每名教职工要关注每一个、发展每一个、成就每一个,让每位双语学子都能成为双语学校一张行走的名片;每名干部要秉持“发现人、鼓舞人、成就人”的姿态,团结好队伍、团结出向心力、团结出战斗力,不断提升家长和社会对学校办学的满意度和体验度。他表示,只有认知的突破才能收获真正的成长,能力永远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和后台,双语的教职工要勇于跳出舒适圈,不断突破自己,成就更好的自己。
最后,他将四句话送给全体教职工: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节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
会上,学校校长孙青从现状分析、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与分项目标、实施路径与保障措施五个方面深度解读了学校三年发展规划,以前瞻性的战略部署和系统性的顶层设计,描绘了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她运用SWOT分析法深研学校现状,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为引领,紧密契合教育强国建设的新时代诉求,找准发展定位,以集团新十年战略行动与主题研究为指引,在“办一所济南市高品质的顶尖学校”的总体目标引领下,深刻阐述了“高品质”的四维内涵:格局大、视野宽、品位高、质量优,带领全体教职工贯彻“追光者精神”,靠近光、追随光、成为光、散发光,让教育之光照亮自我、学生、家长与团队。
未来三年,学校将瞄准高品质的教育质量、文化和管理、教师队伍、课程体系、课堂教学、家校共育、服务保障七维发展目标,共同实现学校的高定位与高品位建设、高质量与强品牌发展、强认同与优体验服务,将历山双语学校建设成一所面向未来、创新发展、受人尊敬、值得信赖的新质学校,以奋斗实干重构未来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态!
她指出,未来三年,学校实现“高品质”建设与发展,体现在学业成绩、学业素养、精神面貌“三高”的教育质量上;体现在高品质文化体系搭建和民主、科学管理上;体现在具有“教育家精神”,学习型、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上;体现在特色品牌课程和高品质课程体系建设上;体现在数智赋能思维发展型课堂建设和“教学评一致性”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上;体现在家长和社会对学校高度的认同感、体验度和满意度上;体现在高质量的后勤保障服务等多个方面。
报告尾声,孙青以一首《若月亮没来》,激励全体教职工不惧挑战,笃行不怠,在新学期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教育事业,共同谱写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张茜、王伟伟、王宁宁、田学文、刘宝元五位教职工代表分别就规划解读发表感想和体会。
本文链接:http://www.gihot.com/news-8-1565-0.html擘画发展新蓝图 追光逐梦向未来 ——历山双语学校2025年高品质发展大会
声明:本网页内容由互联网博主自发贡献,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天上不会到馅饼,请大家谨防诈骗!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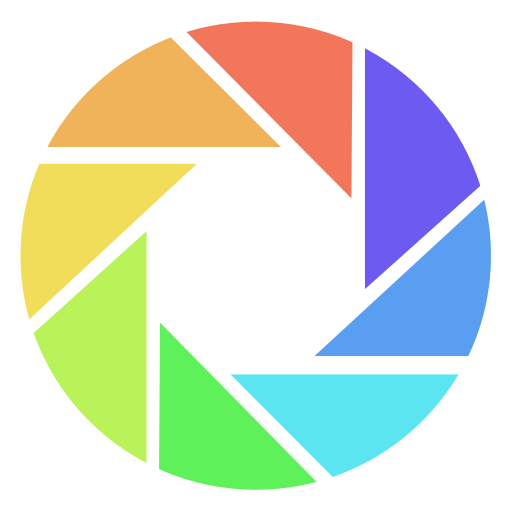 朋友圈
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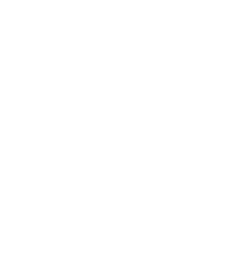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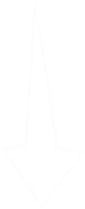
点击右上角 QQ
Q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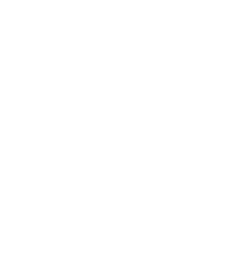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QQ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QQ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